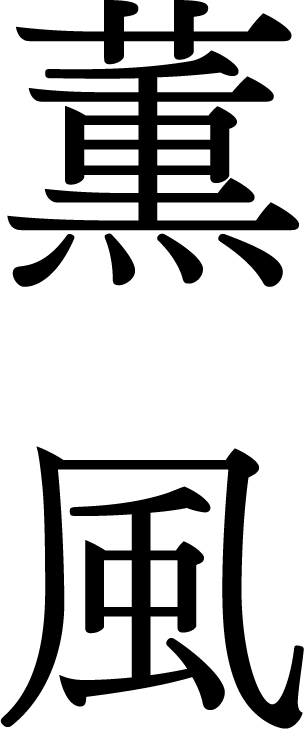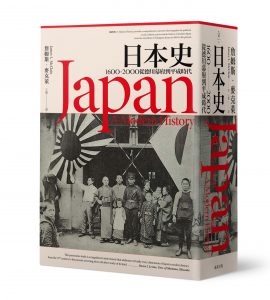
書名:《日本史:1600~2000 從德川幕府到平成時代》
作者:James L. McClain
譯者:王翔
出版:遠足文化
語言:中文
初版:2017年5月17日
因為喜歡說故事,所以跟朋友們一起創辦了「故事:寫給所有人的歷史」網站。剛剛出版了一本書,叫做《大人的日本史》,期待有一天能以台灣為起點,描繪出屬於未來的全球歷史。
在日本近代歷史上,美國扮演過兩次極為關鍵的角色。
第一次是1853年,培里將軍率領著軍艦,一路開到了日本的大門口。這個遠道而來的客人,以武力作為後盾,要求日本簽下《日美和親條約》,逼著兩百多年來只與外界維持低度互動的日本改弦易轍,從一般人所稱的「鎖國」,邁向了開國。
第二次則發生在二次大戰之後,戰敗投降的日本,成為了美軍的佔領地。這一次,推動日本命運轉折的,換成了著名的麥克阿瑟將軍。在他的領導下,日本度過了那段被佔領的時光,也向戰爭之前的帝國時代揮手告別,迎接了新時代的新制度,以及一個新的社會。

率領「黑船」叩關日本的Matthew Perry(1794-1858)

美國隨軍畫家Wilhelm Heine描繪的黑船來航景象
美國雖然與日本近代歷史的關係如此密切,但美國對於日本歷史的研究,起步卻晚得多。二戰之前,雖然已有零星的作品出現,但比較具規模的現代學術研究,幾乎是到第二戰之後才陸續出現、形成氣候。
儘管時間不長,過去幾十年間,美國的日本歷史研究已經累積了可觀成果。詹姆士.麥克萊的這本《日本史》,英文原著出版於2002年,其中便援引了大量美國同行精心撰述的作品。閱讀本書,正好也可一窺美國學術界對於日本近代史的用心之所在。
麥克萊教授自大學開始接觸日本文化,1979年於耶魯大學取得博士學位,之後在布朗大學任教,迄今已近40年。他以研究日本近代城市史出道,但首部作品寫的不是東京或京都,而是位於日本海側的金澤。到了第二本書,他才把目光移回了首都東京。值得一提的是,這本由他與其他學者主編的書,為東京研究挑選了一個十分具有啟發的視角,也就是把東京(江戶)與法國巴黎相互比較,為這兩座一東一西的城市,找出了歷史上的許多相似之處。
原來,在17、18世紀,或者是學者口中所稱的「近代早期(early modern period,在日本學界一般稱為「近世」)」,東京與巴黎都歷經快速成長,也面臨著隨之而來的種種問題。這些都市發展所衍生的問題,刺激日本與法國的當政者強化統治的手段,也促成了國家體系的發展與成長。
這種把日本放回世界史、把日本與歐美歷史相提並論的視角,可以算是晚近歷史研究的一大突破。在這種視角下,日本不再只是那個在近代拼命追趕歐美的封閉落後國家,相反地,儘管在培里來到日本之前,日本人與西方世界接觸不多,但在這種相對獨立的環境下,江戶時代的日本仍然在社會經濟上獲得了可 觀的發展。在本書中,麥克萊引用了以下的例子,正凸顯這一點:
「對住房風格和舒適度、服裝、飲食的考察表示,19世紀中葉,大多數日本人家庭生活條件可以和工業革命前夕的英美兩國相比。在這方面值得一提的,還有出生於近世早期末葉的日本人平均壽命大約和出生於1840年的西歐人(男性39.6歲,女性42.5歲)一樣長,略高於1850年出生的美國人(男性37歲,女性39歲)。」(頁117)
擁有世界史視野的日本史寫作,還有第二個特色。很長一段時間,不管在日本國內外,研究日本史時,經常傾向強調日本歷史的特殊之處。從這樣的角度出發,寫出來的歷史,自然會不斷強調日本的與眾不同,差別只在於,喜愛日本的人主張日本文化是與眾不同地好,討厭日本的人則會說它是與眾不同地壞。
麥克萊和他同輩的學者,逐漸擺脫這種把日本歷史和文化本質化或獨特化的傾向,改而強調日本與外在世界互動過程中不斷產生的變化。正如麥克萊在本書伊始引用著名人類學家格爾茨(Clifford Geertz)所言:「理解一個民族的文化,即是在不削弱其特殊性的情況下,昭示其常態。」
理解這一點,我們就能理解為什麼本書原著的標題是「Japan: A Modern History」(日本的近代史),而不是「Modern Japan: A History」(近代日本史)。乍看之下,兩者相去不多,但其中差異卻微妙地表現了不同的歷史視角。前者是把日本看成世界近代史有機的一環,也因此,在描述日本這個國家過去四百年的經歷,不只是讓我們看見日本自身的歷史,也就是藉由日本這個案例,讓我們在理解近代世界的變化時,有了新的視野。
這是許多美國的日本史學者念茲在茲的問題,他們一方面要對身在日本的日本史同行說,日本史離不開世界史,一方面要對在美國研究世界其他地區的歷史學者說,世界史的寫作不能少了日本史。
喜愛日本文化的台灣讀者,想必可以從麥克萊的這本《日本史》獲益良多,這是一本極為清晰而豐富,充滿著生動細節的近代日本史教科書,全書篇幅超過八百頁,能將這樣的書譯介至華文世界,確實難得的工程。不過,其中也難免有些小錯誤,比如第11章談到幸德秋水與菅野須賀時,便把兩個人的角色弄混了。
另外,值得注意的一點是,台灣在本書中很少被提到,甚至在描述日本帝國的海外擴張時,台灣也只是被匆匆帶過。這固然是作者個人的選擇,但也反映英語世界的日本史研究中,台灣的能見度並不高,能夠參考的著作也很少。這一點,恐怕也還有待來者努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