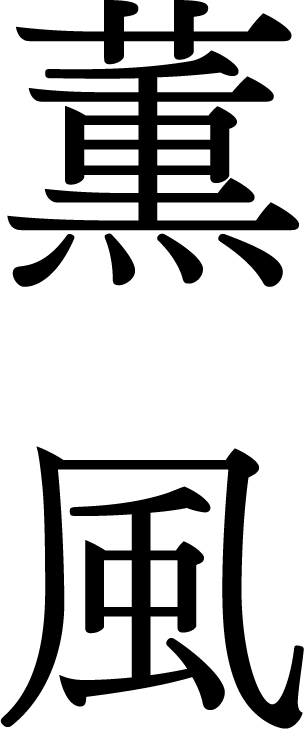© 姚銘偉
當台灣朋友得知筆者在日本工作後,往往第一句話就會問:「在日本上班很辛苦吧?」第二句一般就接著問:「是不是下班都要跟同事去喝酒應酬到很晚?」
通常我的回答是:「在日本常常應酬喝酒的公司肯定是有,但並不是我的生活經驗。」而筆者身邊的日本朋友、同事,喜歡下班和同事聚一聚的也是有,但絕不是強制或普遍的例子。

© Takamorry
單就個人有限的生活經驗,可能流於主觀;但從數據上來看,2017年12月《日本經濟新聞》針對職場新鮮人(新入社員)做了一項調查,發現其中41.5%上個月完全沒有和上司應酬,而36.5%僅僅只有一次。與上司應酬理想的次數,40.3%的受訪者回答了「一個月一次」。當然,這項數據是針對第一年職場新鮮人,也包含了所謂的「寬鬆世代」(ゆとり世代,出生於1987~2004年),但全體的職場面貌,我認為也確實往這方向靠攏。
現今日本的年輕世代,主要分為兩者:一是上段介紹的寬鬆世代;二為筆者也算是一員的「冰河期世代」(1970~1986年)。這兩個世代是日本職場的年輕新血,很大程度也將構成日本企業的未來。
冰河期世代,也是我認識最多的一代。他們分成兩個階段,1970~1975年出生的,是戰後第二次嬰兒潮(部分原因跟泡沫經濟有關);而1976~1986年則是「團塊世代」(戰後第一次嬰兒潮)的小孩,數量上也很驚人。但這一代人,在面臨就職的時候,原本就人數多、競爭大,更恰好遇到泡沫經濟破滅,及之後的長期經濟衰退,日企紛紛減招、甚至裁員。這樣寒峻的就業環境,在日本又稱之為「就職冰河期」。
也因為這樣的環境,讓冰河期世代有著截然不同的思維。在就職的前後,目睹了大量企業倒閉和裁員,這個世代開始思考,並不是完全照公司、上司的話去做就可以保證人生無憂。而終身雇用制的破滅,更讓這個世代赫然發現,那些在公司的人情網絡,在轉職時一點都派不上用場。所以這個世代,比其他世代更追求專業技能和證照,相信不斷提高自己的專業能力,才是在冰河期存活下來的根本。

© Seb
而寬鬆世代成長的環境,就已不像冰河期世代這樣嚴峻;教育課綱的修正和授課時數的減少,讓寬鬆世代在成長過程中,有更多時間去探索自我。對比冰河期世代的忠於自我,是環境逼迫下為了存活不得不為的選擇;而寬鬆世代的忠於自我,則是認為人生的目標不僅僅在於地位或收入,信念的實現反而更加重要。
我所認識的寬鬆世代,的確有許多人選擇了與以往出人頭地之路(出世道)截然不同的方向。他們進入了各種非營利組織,從事人道關懷、社福和環境保護。即便是進入傳統職場的寬鬆世代,也多半強調工作和私人時間的平衡——負責的部份做好就好,非工作時間所培養的興趣同樣重要。而人際關係方面,比起公司的階級關係,他們更在乎社群網路(SNS)上的互動。
兩個世代構成了現今日本職場的年輕風貌。逐步晉升為管理階層的冰河期世代,原本就強調培養自身實力,把許多工作外的時間都投入增進專業技能或培養第二技能,所以喝酒應酬不再是人生的優先目標;而寬鬆世代則著重工作和生活的平衡,做好份內的事情、享受精彩的人生,當然對傳統的應酬文化敬謝不敏。
於是第一線主管對應酬興致缺缺,部下也對社內的交際幾乎無感。在這樣的背景下,回頭看《日本經濟新聞》的統計:「新入社員有41.5%上個月完全沒有和上司應酬」,這樣的結果也就不令人意外了。
當然飲酒應酬只是一件小事,但在這件小事上反映的是兩個年輕世代的個性和選擇。當時間逝去,這些世代進到決策核心、開始帶領日本企業向前邁進的時候,或許我們所感受到的日本企業,又將呈現截然不同的面貌。